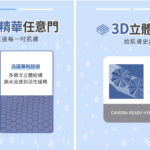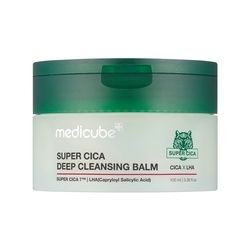台灣夏季氣候潮濕炎熱,戶外烈日的紫外線曝曬容易使肌膚曬紅曬傷、曬黑曬老,進了室內雖有冷氣降溫,乾燥的冷空氣卻容易使肌膚缺水。無處不在的空氣髒汙,隨時降低肌膚抵禦力,這些室內室外的傷害,讓你肌膚老化的速度比你想像中還要快!
擁有百年歷史的肌膚保養專家凡士林,今年在炎熱酷暑來臨前重磅推出品牌第一支身體防曬新品:凡士林5D極護水感防曬乳。
凡士林第一支超越防曬的5重防護力最頂新品,將傷害肌膚的5種隱形殺手:UVA、UVB、光老化、空氣髒污、冷氣乾燥通通一網打盡,今年夏天,一支凡士林 5D小橘傘為你撐起防曬的多重防護宇宙,讓你成為人群中的白皙女王!

零著感極輕盈防禦 5重防護力抗曬x養膚同時完成
凡士林5D極護水感防曬乳除了擁有高規格防曬係數SPF50+ PA++++,170ml超霸容量更是直接挑戰市場最高CP值,讓你出門在外即使瘋狂補擦、全家大小一起使用也不心疼!
除了肉眼可見的超強防曬力外,產品三大特色有:
– 零著感隱形科技:
身體防曬最怕黏!凡士林特選水油雙相防曬成分,打造滑順易推開,不黏膩,輕盈水感不悶黏的優秀質地,提供肌膚最輕盈的超強防禦,特別適合台灣悶熱的夏季
– 3重維他命精華:
添加菸鹼醯胺、維他命C、維他命E,三重維他命精華,讓你在防曬同時更能養膚,對抗冷氣房帶來的肌膚乾燥,幫助延緩肌膚老化,強韌肌膚屏障
– 無添加:
凡士林秉持肌膚保養專家的專業精神,無添加酒精及色素,給你最安心的守護!
拒絕曬紅曬傷、曬黑曬老,一次揮別暗沉、曬後斑點等肌膚光老化問題,交給肌膚保養專家凡士林5D極護最安心。擁抱水潤零著感的白嫩柔滑肌,成為今年夏天耀眼的白皙女王!

新品上市優惠價%促銷檔期資訊!:
– 屈臣氏:
5/16~6/12 NT$199 (原價 NT$399)
6/13~7/10 NT$229 (原價 NT$399)
– 康是美:
5/17~6/20 NT$229 (原價 NT$399)
6/21~7/18 NT$199 (原價 NT$399)
– 寶雅:
5/9~6/4 NT$229 (原價 NT$399)
6/6~7/2 NT$199 (原價 NT$399)
– MOMO:
上市價 NT$299 (原價 NT$399)
活動促銷優惠價以最終通路公告及結帳為準

5D極護水感防曬乳SPF50+ PA++++
標題:【Vaseline 凡士林】今夏防曬天花板! 凡士林首創。5D身體防曬 全波段~阻隔 一支抵抗光老化 曬不黑也曬不老 /
鄭重聲明:本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,轉載文章僅爲傳播更多信息之目的,如有侵權行爲,請第一時間聯系我們修改或刪除,多謝。